
“我情愿忘却自我,而只讲述能够彰显强势人物的事情。”——兰克《英国史》第2卷
他的学说影响了傅斯年、陈寅恪和姚从吾
都说历史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所*****,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面目模糊。可这位历史学家,却坚信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并对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他就是利奥波德•冯•兰克,德国历史学家,被公认为“近代历史学之父”。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出生于一个虔诚信仰基督教的中产阶级家庭。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出版后,兰克一举成名,受聘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在长寿的一生中,兰克治史范围广阔,完成了数量惊人的历史著作,仅其在生前亲手编订的全集,就有54卷之巨。他提倡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理想,首创学术专题研讨班制度,对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被公认为“近代历史学之父”。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1月出版了其影响深远的《近代史家批判》。
许多论文(见凤凰文化《兰克诞辰220周年:傅斯年、陈寅恪是兰克的继承人?》中引用的论文)研究认为,兰克的学说,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史学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比如说,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1929年9月,他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除此之外,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认同兰克在治史方面提倡的客观主义,更将其付诸实践。历史学家姚从吾更是把兰克研讨班教学研究形式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兰克史学的深远意义。
“忘却自我”是他一生心愿
利奥波德·冯·兰克比19世纪任何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都更强调科学“客观性”。这是有据可查的。实际上兰克“忘却自我”的说法也许正是对这位潜心钻研其学术的历史学家最为贴切的比喻。
“客观性”在这里应理解为走出自我、不加任何其他补充的对于客体的描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是对以往现实的一种写照。
兰克有一句在世界范围内常被引用的名言:“历史学家“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语出自兰克《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一书的前言)
不过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兰克的这个“愿望”过于天真。比如和兰克同时代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在其《历史知识理论》一书中就指出,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再现的。历史不是以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以迄今为止的流传为基础的:这就是历史的出处。此外,他还指出,历史学家不可能也不允许忘却自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寻找有关过去事情的原始资料,对原始资料加以解释并说明这种解释的含义之所在,以便读者能够获悉事物的全貌。
在这些评论面前,兰克的客观性注重乍看起来确实显得不切实际。不过,针对兰克的所有指责都没有涉及兰克本人是否在其理论指导之下对于历史事件作出过错误主观的判断,抑或在有关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分析方面存在问题。人们只是评论兰克“客观性”概念本身的天真和不切实际,但并没有指责兰克其人。
相反,后来的历史学家倒是常常援引和和运用兰克的“客观性”概念。兰克的“客观性”概念基于19世纪上半叶对于历史的普遍认识。兰克主要是从理论上强调并使用“客观性”这个概念,他并没有把“客观性”纳入自己实际研究的范畴;他很滑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他曾经这样写道:“我提出了一种理想,人们会对我说,这种理想无法实现。但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无限,但他所能取得的成就天生有限。”(兰克:《思考》,第14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是把历史客观性视为一种理想,一种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然而又是永远难以实现的理想。
培养历史文化的真正代言人
兰克的名字还和历史学的学术机构密切相关。特别是他创立的历史研讨班,更是闻名遐迩。在这种研讨班里。学生们学习如何的批判性地对待史料,并被而有望成职业的历史学家。这些学生受到良好的专业培训而有望成为各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真正代言人。
同时,兰克强调,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具有艺术活动的特点。他写道:“历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同时也是艺术”由此,兰克提出了一个直至近几十年来才被专业历史学家视为不言而喻的主张,亦即,修辞严谨和文笔优美的历史著作对于认识和研究历史十分重要。
然而,兰克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科学的这种双重特点。他曾经这样写道:“历史科学要对事物进行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艺术则是对所发现、所认识和所发生的事物进行叙述。”在这里,兰克对于历史学工作用了三个动词进行概括,即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这是兰克对历史学的核心工作程序所做的天才概括。
下一篇:演员钱芳的演艺经历有哪些
相关推荐
-
 傅雷之子傅敏回忆往事
傅雷之子傅敏回忆往事许多人都知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对这个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傅敏却知之甚少。傅敏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
2020-04-30 -
 傅斯年和胡适当年为什么去台湾?去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傅斯年和胡适当年为什么去台湾?去台湾的目的是什么胡适一生身居高位,影响力巨大,**上常年屈服*****,赞成*****对自由人士的屠杀,这是胡适的**表现。在学校里作为北大校长,打压进步学生。有著名的冯挺杉事件。傅斯年
2020-04-3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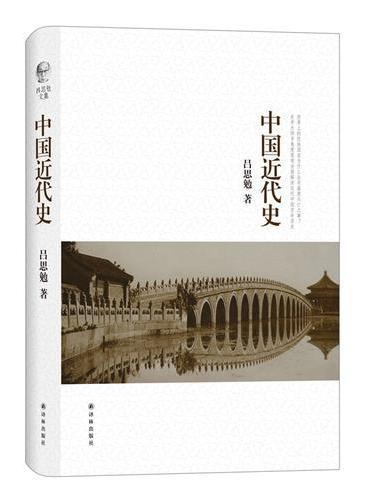 吕思勉著作《中国近代史》出版
吕思勉著作《中国近代史》出版吕思勉(1884~1968),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先后曾在常州府中学堂、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包括后
2020-05-01 -
 西门庆扮演者 杜淳版的大官人你喜欢吗
西门庆扮演者 杜淳版的大官人你喜欢吗四大名著都被拍成电视剧了,而《水浒传》被经常翻拍的一部经典,无论是作为电视剧还是电影。而最近翻拍的《水浒传》里面的西门庆是由杜淳演的,据说很多人看完杜淳饰演的大官人,心情是复杂的。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西门庆扮演者杜淳吧。
2020-05-01 -
 裴涩琪整容了吗 裴涩琪个人资料
裴涩琪整容了吗 裴涩琪个人资料裴涩琪整容了吗是很多网友想要了解的问题,那么韩国歌手裴涩琪究竟整容了吗?关于裴涩琪的个人资料你又了解哪些呢?下面是小编带来关于裴涩琪整容了吗的内容,希望能让大家有所收获!
2020-04-20 -
 romantic什么意思 romantic是什么
romantic什么意思 romantic是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学起了英语,于是学习最基本的英语单词便成了人们学习英语的起点,但是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懂得单词,比如,romantic什么意思 romantic是什么,下面小编来为大家解答,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20-04-30


